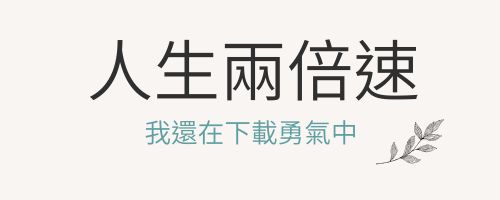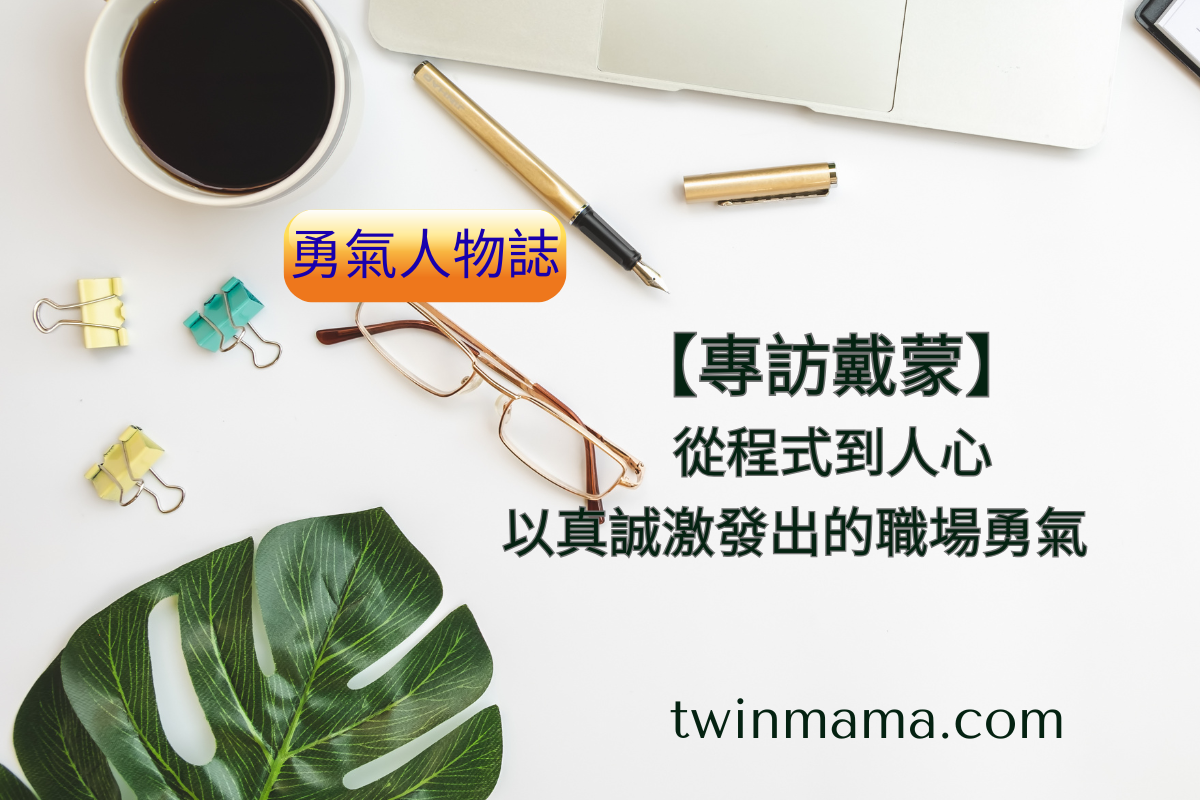我坐定位之後,戴蒙還沒出現,我心中想著他會不會又穿同一件外套?他出現時,神色略帶了一些緊張,我笑著說:「你果然又穿著這件外套。」
這就是戴蒙,總讓人放鬆,卻又很難真正看透。他不太習慣被這樣邀訪,第一句話是:「我不是什麼大人物,妳寫我會有人看嗎?」我回他一句從文案老師那學來的話:「平凡人的故事,只有平凡人最懂得感動。」
如果你也曾在工作中懷疑自己的價值,那麼你會明白,哪怕只是一個願意陪你做小事的主管,都可能成為你職涯中最大的貴人。對我來說,戴蒙就是那個人。他總是手把手地陪我完成一件件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任務,用一種很誠懇的方式,讓我相信:在這個讓人想逃的職場裡,我其實還能做得不錯。
快速解決~直接點開連上
他不是超級業務,卻讓人願意跟著他走
已故的蘋果公司創辦人史蒂夫‧賈伯斯總是穿著同樣的黑色高領毛衣與牛仔褲。那天,當戴蒙一走進來,還是那件熟悉的深藍外套,我忍不住笑了出來,心裡想著:他是不是也像賈伯斯一樣,對衣著毫無興趣,只想把腦袋的空間留給更重要的事?
只是又有點不對勁。賈伯斯給人的印象,是個偏執冷峻的技術宅;而坐在我面前的戴蒙,卻是個話匣子一開就停不下來的人。從我們坐下的那一刻,他便滔滔不絕地和我聊起他從高中到碩士的求學歷程,語氣就像在介紹自家倉庫裡的藏品,一樣熟悉,一樣自信。
我忍不住問他:「你應該是很會聊天的人吧?」
他搔了搔頭,笑得有點不好意思。
「其實我不覺得自己會聊天耶。不像那些超級業務,可以在各種人面前切換自如,我沒有那種能力。可能是當主管久了,覺得要主動去關心人,再加上我有點雞婆啦,什麼事都想插一腳,分享一下自己以前怎麼做的。如果這樣也算會聊天,那可能就是了吧。」
我看著他,腦海浮現那些他在公司裡主動伸出援手的片段。有些人是真的擅長交際,而有些人,是因為想幫忙,所以努力學著怎麼靠近別人。戴蒙顯然是後者。
他還笑著補充了一件我沒聽過的小事:他同一種早餐可以吃三年不換,進早餐店只需要說四個字:「一樣謝謝。」說完他自己先笑了,說自己就是標準工程男,無趣、不懂浪漫,也不會搞什麼驚喜。
我聽著,默默地想,其實這樣的穩定,某種程度也讓人安心吧。只是我還是忍不住想問——你從來沒想過,自己是不是選錯了路嗎?沒想過走這麼務實的路,會不會太沉悶了點?
然而當他談起「程式邏輯」這個詞時,我突然注意到他眼神裡的光。他說,那是一種可以讓複雜問題變得清晰、井然有序的魔法。也是這份邏輯,讓他在每次轉換跑道時,不至於迷失方向。
也許,對他來說,穿什麼根本不是重點。因為他早就穿上了自己最熟悉、最實用的「解法」過日子。
說到底,那天我真正想問的不是「你會不會聊天」,而是:「你是怎麼讓人感覺被看見的?」後來我想,或許答案藏在他自己都沒發現的小動作裡——在走過走廊時的招呼聲,在你抱怨時他靜靜聽你說完的神情,在他願意為了解你而多問一句「還好嗎?」的態度。
如果你也覺得自己不擅長社交,其實不用強迫自己變成健談的人。很多時候,真正讓人舒服的溝通力,不是說得多漂亮,而是「我願意花時間理解你」。
溝通從來不是一場表演,而是一場靠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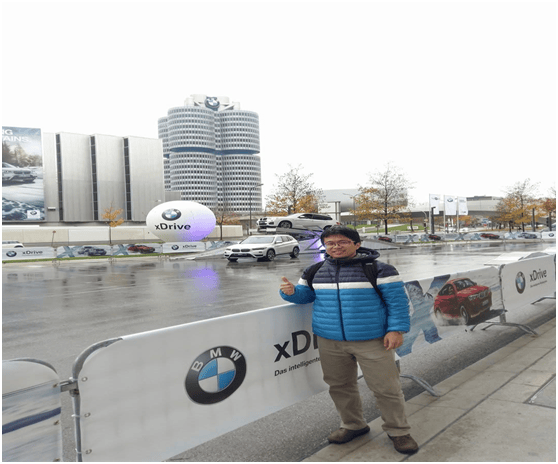
我請戴蒙提供一張照片讓我放上文章,他說自己自拍照片不多,免強給了我張10年前的充數。我笑他這張看起來傻,不像個睿智主管。然而10年前的他,也正在蓄勢待發,帶著他的程式腦,勇敢前往未知的職場叢林探險。
轉職轉部門、撐過困境:他不是天選之人,只是很會撐
那年是民國九十八年,金融海嘯剛過,社會上瀰漫著一股找不到工作的焦慮。戴蒙就在那一年碩士畢業,推著履歷走進一個不友善的大環境,起薪只有2.7K。不是他不努力,只是運氣不站在他這邊。那個年頭,學歷像是失了效的門票,投遞出去的履歷總是沒有回音。他說他早早就告訴自己:可能沒辦法找到「理想工作」,但至少要把第一份工作當作「生存的起點」。
他形容自己像在玩一場程式遊戲,只要拆解出邏輯,總會找到一條活路。這樣的態度,也成了他未來升遷的核心能力——適應。六年內,他在同一家公司經歷了四次轉職,每次轉換職位,都帶著更多的責任與挑戰;也每一次,他都用實力證明自己走得來。如今的他,已是員工破千的上市櫃公司總部副廠長。
「不能輕言放棄,讓相信我的人失望。」他這樣說。語氣平穩,卻字字沉重。
我問他:「你原本想當主管嗎?」
「工程部是我初入這家公司時的單位,這是我的專業,那時候很單純,只負責搞產品做好就好。妳問我成為主管是不是自己的選擇?老實說我還真的沒有想過當主管,只要公司看得起我,我就不能讓公司失望。」
這樣的信念聽起來有點傻氣,卻也誠懇。就像我們總以為「貴人」會一直站在你身邊、給你打氣,事實卻不然。
「我當然非常不能理解,他居然跟別人站在一起找我麻煩,他不是找我來幫他的嗎?怎麼會全部變成我在扛。當時的我從工程部被調到業務部,我覺得很痛苦,因為那並非我擅長的,所有的人都在挑戰我,這過程也曾經一度想放棄。但是當問題來臨時,在完全沒有前人可以指導的狀況下,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決。」
然而也正因為沒人能依靠,他逼著自己在混沌中摸索解法。他說:「當你撐過那段痛苦的過程,這些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。」
說這段話時,他輕輕地曬了曬手上的錶,那是某次挑戰後的獎勵,也是一個提醒。那次,他被升上高階職位,空降進一個從未接觸過的領域,立刻被要求完成一場從沒預演過的試量產。他準備萬全,卻在最後一刻,治具出問題。他沒有責怪誰,只是抱著壞掉的治具,衝去廠商那裏求救。模具廠的夫妻看他如此焦急,選擇整夜沒睡,陪他一起趕工。第二天清晨,他帶著修好的治具回到公司,也帶回一場即將失敗的危機,奇蹟般地逆轉。

這是在當時戴蒙所負責的產品,轉任業務時購買,對他而言很有意義。
在職場裡,不一定所有的轉機都會有預兆。有時候,我們以為是被拋棄,其實是被放進另一個考驗中。當我們也正被調離熟悉的位置,不妨試著問自己:「這是不是一種看見自己潛力的新方式?」「我要靠誰?還是,我能不能靠自己?」
而我在戴蒙身上所學到的是:
1. 接受混亂是常態。
2. 用拆解任務的方式來降低不安。
3. 把過程當作累積經驗值的副本,每破一關,未來就少一點害怕。
或許我們都曾在職場裡懷疑過自己,也走過那些被丟進陌生領域的時刻。當時我們也會害怕、也會氣餒,甚至懷疑是不是自己不夠好。但慢慢地,我們總會發現:原來混亂不是壞事,而是一種成長的訊號。
他怎麼看員工?你可能也在這兩種人之間
訪談快要結束時,我忍不住問了一題採訪者的特權問題:「你心中最理想的工作夥伴,是什麼樣的人?那我算嗎?」
他的眼神開始飄移,像是突然被點名的學生,支支吾吾地找出口。
「對我來說,沒什麼主見的員工反而是公司的中流砥柱,只要給出明確的指令,他們就會很穩定地運作。但也不能期待他們帶來什麼創新。」他頓了一下,看向我,「不過,有想法的員工就一定要放在對的位置,不然就會變成管理上的挑戰……妳是有想法的那一種。對了,情緒控管——那會決定一個人是不是可用之才。」
其實我早就知道,我在他心中並不是一個「好帶」的員工。
在他出現之前,發脾氣是我用來保護自己的方式。我曾以為那是生存的必要技能,直到他出現,我才第一次感受到,原來我也能用正常的語言,去說明自己不滿的地方。那種「不需要用怒氣才能被聽見」的感覺,對當時的我來說,像是一場意外的和解。
而他看我時那一臉「不知道該不該講實話」的尷尬模樣,老實說,現在想起來還挺好笑的。
或許,你也會像我當時一樣把「情緒」當成自保的工具,以為只有強硬才能爭取空間。但其實,當有人願意用理解取代壓制,那些曾經緊繃的情緒,也會慢慢被鬆開。
如果你現在也正處於「不知道怎麼好好表達自己」的階段,不用急。不是你不夠好,也不是你太情緒化,可能只是你還沒遇到一個,願意聽你說話的人。
我們都會慢慢學會的,不是壓抑情緒,而是找到讓人願意聽的方式。
名片之外,他留下的,其實是勇氣
離開前,我問了他一個問題。那個問題,並不在訪綱裡。
聽到我丟出的題目,他顯得有些不知所措,因為問題太宏觀了。他還是試著從腦海裡翻出些什麼,引經據典地回答我。我說:「喔,好失望喔!」
他大概以為我期待一個更有深度的回覆,便又努力換了一個版本,說完還問我:「這樣妳懂嗎?」我笑著回:「我正在用你的話,轉成我能(也願意)懂的版本。」
在我腦中來回轉換的那一刻,我忽然忘了自己到底問了什麼。
也許我真正想知道的,不只是他的答案,而是──當有一天,他不再擁有名片上的頭銜,他是否還有力氣繼續奔跑?因為對我來說,在那段時間裡,失去他的支持,就像失去了努力的資格。
「我一直惦記著你們廠門口那兩根柱子。如果可以待久一點,我一定會想辦法把它們換掉。剛來的時候,我真的很開心,因為我終於有更多可以改變環境的權力。」
他說起那兩根柱子的神情,讓我記起了他調回總公司的那天。
他離開前的最後一刻,還在替我們廠門口掃地。掃完,他拍了拍手,笑著說:「以後我退休了,來當守衛也不錯啦。」
那天的陽光很刺眼,我記不得自己回了他什麼,但是他的舉動令我很是感動。
因為在他身上,我總能看到一種本事──不論身處何處,他總能找到一條出口。
而我,也想在他的回答裡,找尋屬於我的那一條。
是他讓我開始相信:就算環境不理想,只要我願意,我也能成為改變它的人。
於是,我開始練習,一點一點地,找回自己的力氣。
有些改變不是從看見機會開始的,而是從「有人相信你做得到」的那一刻開始的。
當你曾經被誰點亮過,也就會想努力成為自己的光。
如果你正在一個灰灰的時候,那我們就先一起慢慢找回那盞燈。
不急,我們不必馬上變好,只要還願意繼續走,人生就會慢慢回暖。